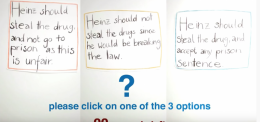呂偉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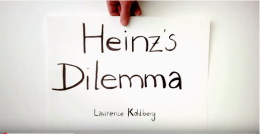
柯伯格的道德兩難故事─漢斯偷藥
柯伯格的道德兩難故事是修過教育心理學的人的都聽過的故事。這個故事大致是這樣的:有一個叫做漢斯的人,他的太太得了不治重病,命在旦夕。這時,只有一個藥劑師發明的一種新藥可以救她,但是這個藥劑師索價10萬元(雖然製藥成本只有1千元);而漢斯只有籌到5萬元,於是漢斯哀求藥劑師將藥價打對折,或者是讓漢斯先付5萬,剩下的5萬日後償還。但是冷血的藥劑師並不同意。於是漢斯晚上潛入藥房,偷了藥回去救他太太。

在柯伯格的跨國家、文化的研究中,他問受試者下面四個問題:
1. 漢斯是否應該偷藥?
2. 如果漢斯不愛他太太,是不是他就不會去偷藥?
3. 如果生病的是漢斯不認識的人,漢斯是否還會去偷藥?
4. 如果漢斯的太太因得不到新藥而死的話,警察是否該逮捕藥劑師?
柯伯格根據受試者的回答,主張人們在不同時期對於兩難問題有不同的推理,而這樣的推理順序是跨文化、人種與性別的。他將道德的發展分為以下三個主要階段,而每個階段下面又分為兩個次階段,所以總共有六個階段:
1. 前習俗道德期:第一階段:懲罰與服從取向,第二階段:相對功利取向
2. 習俗道德期:第三階段:好男/女孩,第四階段:法律秩序取向
3. 後習俗道德期:第五階段:社會契約取向,第六階段:普遍倫理原則
下面這個互動式的動畫影片對這個故事有基本的介紹,看完故事,點選你的觀點,就會得知你是處在柯伯格道德論的哪一個時期。
柯伯格的研究問題並不是兒童對於漢斯是否該偷藥答「該」或「不該」,而是這樣回答的背後的推理何在。下面列出不同的回答也可能處於同樣的推理階段:
• 第一階段 (懲罰與服從):
– 漢斯不應該偷藥,因為這樣一來,他就會被關到監獄,壞人才會被關在監獄。
– Or:漢斯應該偷藥,因為這只值1000元,藥商索價太高,漢斯也願意付錢,而他也沒有偷其他東西。
• 第二階段 (相對功利):
– 漢斯應該偷藥,因為他救了他的太太他會感到快樂,即使他會被關在監獄中。
– Or: 漢斯不應該偷藥,因為監獄是一個糟糕的地方,他被關到監獄的境遇會比遭遇太太病死而更悲慘。
• 第三階段 (好男孩/女孩):
– 漢斯應該偷藥,因為他的太太希望他如此,而他希望自己是一個好丈夫。
– Or: 漢斯不應該偷藥,因為偷竊是不好的行為,而他並不是一個罪犯,他應該嘗試不違反法律的其他方式。
• 第四階段 (社會秩序):
– 漢斯不應該偷藥,因為法律禁止偷竊,這是犯法的。
– Or: 漢斯應該為了救他的太太而偷藥,但是也應該受到懲罰,而且付藥商藥錢。罪犯不應該無視於法律,他必須為這樣的行為付出代價。
• 第五階段 (社會契約):
– 漢斯應該偷藥,因為每個人都有權力選擇生命,無論法律是怎麼規定。
– Or: 漢斯不應該偷藥,因為科學家應該有公平的補償,即使太太生病,這樣的行為也是不應該的。
• 第六階段 (普遍倫理):
– 漢斯應該偷藥,因為拯救人類的生命較之其他人的財產有著更重要的價值。
– Or: 漢斯不應該偷藥,因為其他需要藥的病人和漢斯的太太的生命同樣的重要,而且對藥物有同等的需求。
上文是對柯伯格道德論的介紹, 這篇筆記真正想談的是我於上課講授道德階段論時,一些引伸觀察與發現。在講完兩難故事時,我通常給學生的思考問題是:如果你是法官,你會怎麼判?在我教過的大約10個班中,調查結果可以歸納為:多數同學傾向輕判,但是還是要判;少數同學主張依法論法,極極少數認為應該無罪釋放。這樣的結果顯示多數同學處於第四、五階段之間。如果再加問一句,輕判還是判,那麼,漢斯入獄了,誰來照顧他的太太呢?學生們多會有很有創意的想法:改罰漢斯社區服務─如打掃社區,這樣他就可兼顧妻子了;募款幫漢斯請看護照顧妻子;法官幫漢斯付清藥錢等等。這樣的酌情衡量,也朝向第六階段的普遍倫理的方向。但是,如果進一步的追問:看來漢斯是情有可原的,那麼,判無罪不行嗎?歷年來只有一隻手數得出來同學可以接受無罪的判決,其他的同學多露出對這樣的判決unconfortable的表情。為了證明漢斯被判無罪也可能是合理的結果,我舉美國曾經發生的Mercy Killing的判例,來挑戰學生推理答案可能性的極限。
Mercy Killing 可以無罪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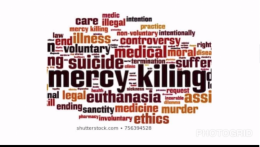
在2001年,美國發生一件先生殺死太太的刑案,先生已經100歲,因不忍見太太頻繁被安置在不同的安養中心,為了不讓太太再遭受轉換環境壓力,於是他殺了太太。法官認為這樣的謀殺是基於”an act of love”,而100歲的案主身心狀態已經處於不正常狀態,使其做出這樣的決定,因此獲判無罪。
另外,在2005年,一位父親在承受中大的壓力之下,以枕頭悶死患有黏多醣症的兒子,最後父親殺人部分獲判無罪,只科以兩年的緩刑。這兩個案子的案主都是在巨大的壓力下,為了抒解他們摯愛家人的痛苦,而做出殺人的行為,在這樣的情況下,殺人者和被殺者都是受害人。而無罪判決說明了:法官還是可以於法條之外,酌情衡量每個案件的特殊狀況,彈性的做出判決。(Ost,2007)
舉Mercy Killing判例的例子,不是支持Mercy Killing一定無罪,而是說明許多事情都是兩難的狀況,同樣的一個故事,可能有多個判決選擇,當法律規章與情、理相悖時,如何做出最明智的選擇,這就是專業高下之所在。
法海與贾維爾─恐龍法官的祖師爺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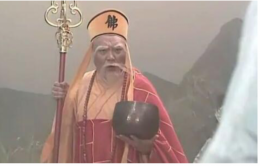

東西方都不乏有關情、理、法之間相衝突的故事。中國的白蛇傳與法國革命為背景的悲慘世界就是兩個例子。追捕白蛇的法海與追捕尚萬強(小偷)的贾維爾(法官)都不得觀眾/讀者的緣。在河南有一座「白衣仙洞」,傳說為當年白娘子成精的地方,香火旺盛受人膜拜,而自認為除妖降魔、拯救蒼生的法海和尚卻為人們唾棄,成為笑柄。
同樣的,在悲慘世界中,曾因飢寒而偷麵包、銀器的逃犯尚萬強,在受仁慈的主教感化之後,存有一顆助人的心,在法國革命中成為正義的化身,最後還上了天堂與主教成為室友;而代表教義、司法,窮盡一生追捕越獄逃犯尚萬強的執法者贾維爾,卻落得難以解決心中情、理、法的糾結,最終跳海自殺身亡。

柯伯格主張將兩難故事設計於學校的道德教育中,我樂見其成。兩難故事可以讓我們瞭解:在真實世界中,多數的事情是沒有標準答案的,每天都可能有兩難問題等著我們,如何維持更有彈性的心,做出最好的決策,考驗著凡夫俗子。